科技工作者之家
科技工作者之家APP是专注科技人才,知识分享与人才交流的服务平台。
科技工作者之家 2021-03-12
来源:衢州科普
△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设立少年法庭办公室,并在六个巡回法庭设立少年法庭巡回审判点。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少年法庭办公室主任杨万明在发布会上表示,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主要负责综合统筹未成年人审判指导,参与未成年人案件审判管理,协调开展未成年人案件巡回审判等工作。
他介绍,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成立后,将围绕低龄儿童犯罪、性侵儿童、拐卖儿童、校园欺凌、虐待儿童、留守儿童监护、儿童信息安全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强少年审判问题研究。
2016年至2020年,依法审理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刑事案件24035件 自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我国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议庭以来,少年法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不断成长壮大。
“经过教育矫治,绝大多数未成年犯悔过自新、重返社会,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和有用之材,少年审判被誉为‘特殊的希望工程’。
”杨万明说。
他介绍,在少年法庭的发展过程中,各地法院积极探索,创立发展了寓教于审、圆桌审判、社会调查、犯罪记录封存、心理疏导、合适成年人到场、回访帮教等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审判制度和工作机制,与此同时,少年法庭的很多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规定。
杨万明表示,针对近年来社会关切的杀害、性侵、拐卖、虐待未成年人,校园欺凌以及利用网络实施的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犯罪行为,人民法院坚决依法严惩,对挑战法律和社会伦理底线、性质恶劣的重大犯罪,该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绝不姑息。
自2016年至2020年,全国法院依法审理拐卖、猥亵儿童、组织儿童乞讨等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刑事案件24035件,惩处罪犯24386人。
切实加强对未成年人权益的民事保护,2016年至2020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结涉及未成年人抚养、监护、探望等民事案件120多万件。
加强未成年人案件问题调查研究,适时发布指导性案例 为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设立少年法庭办公室,并在六个巡回法庭设立少年法庭巡回审判点。
杨万明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办公室成立后,将抓紧研究制定各项制度。
将坚持少年审判的专业化发展方向;加强制度建设,统筹全国少年法庭工作。
同时,加强对未成年人案件问题的调查研究,围绕低龄儿童犯罪、性侵儿童、拐卖儿童、校园欺凌、虐待儿童、留守儿童监护、儿童信息安全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强少年审判问题研究。
及时修改或者制定新的司法解释、司法政策,适时发布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将充分借助专家学者的智慧力量。
“去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少年司法研究基地聘任了首批8位专家委员。
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成立后,我们还会抓紧聘任一批专家委员,推动形成一批有影响、有实效的研究成果。
”杨万明说。
焦点1对强奸未成年人犯罪坚持零容忍立场发布会上,最高法发布7起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何莉介绍了四起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刑事案例的情况,其中包括王某乙强奸案。
该案是一起强奸未成年被害人,情节特别恶劣,受到依法严惩的典型案例。
该案中,被告人为满足畸形心理,在一年三个月内,专门以年龄幼小的在校女学生为侵害对象,教唆多名未成年人予以协助,连续对15名未成年被害人实施强奸,其中8名被害人系幼女,造成多名被害人被迫辍学或转学,人民法院依法对其判处并核准执行死刑。
“需要强调的是,强奸未成年人犯罪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给未成年人的人生蒙上阴影,使未成年人父母及家庭背负沉重精神负担,并严重践踏社会伦理道德底线,社会影响恶劣。
”何莉表示,人民法院对强奸未成年人特别是奸淫幼女犯罪将始终坚持依法从严惩治的零容忍立场,绝不动摇。
何莉表示,近年来,女童受到性侵害的案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但现实生活中,男童也可能受到不法性侵害,也会给男童造成严重心理创伤。
邹某某猥亵儿童案便是一起猥亵男童情节恶劣,受到依法严惩的典型案例。
该案中,被告人利用被害人家长的信任和疏于防范,长期对两名不满10周岁的幼童实施猥亵,手段恶劣,并导致两名被害人心理受到严重创伤,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属于猥亵儿童“情节恶劣”,对其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内从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罚当其罪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焦点2未经监护人同意的未成年人大额直播打赏,可要求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郑学林介绍了三起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民事案例的情况。
未成年人直播打赏、虚拟充值消费等导致的纠纷屡见不鲜,尤其是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亲属账号作出的打赏、购买等行为的合同效力如何认定,引起社会热议。
在刘某诉某科技公司合同纠纷案中,涉案的未成年人使用父母用于生意资金流转的银行卡,多次向某科技公司账户转账用于打赏直播平台主播,打赏金额高达近160万元。
该案经过人民法院多次辩法析理的调解工作,最终双方庭外和解,该公司自愿返还近160万元打赏款项。
郑学林表示,该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司法实践中涉及的网络打赏、网络游戏的纠纷,多数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也就是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这些人在网络进行游戏或者进行打赏时,有的几千、几万,这显然与其年龄和智力水平不相适应。
“在未得到法定代理人追认的情况下,其行为应当是无效的。
”郑学林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对未成年人参与网络付费游戏和网络打赏纠纷提供了规则指引。
意见明确,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该规定更多地考量了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同时引导网络公司进一步强化社会责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网络环境。
郑学林表示,下一步,各级人民法院将深入贯彻实施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反家庭暴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确保未成年人依法得到特殊、优先保护。
来源:新京报编辑:林家骏审核:赵秀应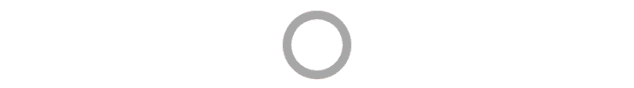


来源:quzhoukepu 衢州科普
原文链接: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ODE3MzU4Mw==&mid=2655359591&idx=4&sn=700e2a166b6231e4a8d2b14e8d1b163d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注明,本站所载内容来源于互联网、微信公众号等公开渠道,不代表本站观点,仅供参考、交流、公益传播之目的。转载的稿件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电话:(010)86409582
邮箱:kejie@scimall.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