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工作者之家
科技工作者之家APP是专注科技人才,知识分享与人才交流的服务平台。
科技工作者之家 2021-04-24

物从其产生之初就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在社会文化内在的冲突、变迁和整合之中。物如何组织欲望?它们激起了什么样的幻想?它们通过哪些经济体获得了新的价值?物如何代表、安慰、帮助以及改变我们的生活?当下我们收集物,是为了使过去与我们相近,是为了将过去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为了使过去遥远,因而物化以获得它的光谱力量?物是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见证者和承载者,而残留在文学文本中的物帮助我们重建文化历史的同时也检验文化和历史的含义。伊迪丝·华顿的《国家风俗》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讲述了一个关于物与主体身份塑造与延续的故事。小说的背景被放置在莱热称之为物的时代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物的发明、生产、分配和消费突然成为定义一个国家文化的决定因素,此时的美国社会在经历了物的匮乏与对物的欲望压抑之后,消费文化开始盛行,“恋物”“拜物”成了人们的生活常态。这是一个物当道的时代,因而需要我们从新的角度观察当时的物质繁荣,建立新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揭示这一关系所隐含的社会文化特征。
与华顿的另外两部描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上流社会风俗和生活画面的长篇小说《欢乐之家》和《纯真年代》相比,国内外学者对于《国家风俗》的研究相对较少。正如保尔·奥勒在《伊迪丝·华顿的“进化观”》中所指出,《国家风俗》中的昂汀更像是华顿这三部纽约小说中主人公心理进化过程的一个断层。从《欢乐之家》中的莉莉到《纯真年代》中的埃伦,女主人公在与现实勇敢对抗之后都实现了内心价值观的成长,然而奥勒又进一步指出,一心想融入纽约都市生活的昂汀为了能够在社交圈中傲人地生存下去,不惜一切代价扫平身边的障碍,正是对“适者生存”这一准则的极好诠释。凯瑟琳·乔斯琳在其《伊迪丝·华顿》中认为,尽管昂汀以“一个有手腕而又坚定的剥削者,一个不知疲倦的女性拓荒者”形象示人,但她所有的快乐、财富、权利、声名却似乎都来自“一个小小的金戒指”。加里·托滕在《记忆的盒子与守护的内在:伊迪丝·华顿与物质文化》中指出,华顿透过在“镜与灯”照射下的昂汀来反映和警示她所看到的当时社会的解体,以及物欲横流的美国社会中人的生存意义的缺失,从而使人们逐渐认清在现代科技的耀眼灯光和炫目反光下必须保存的那些文化价值。劳拉·拉特雷在《伊迪丝·华顿的〈国家风俗〉:一部重评》中提出来自“小地方”的昂汀所受的教育和教养方式使她无法正确认知或应对在老纽约的种种境遇。国内学术界对于《国家风俗》的研究比对华顿的其他长篇小说的研究相对较少。杨金才、王丽明的《老纽约社会的婚姻———论伊迪丝·华顿的纽约小说创作》分析了华顿三部纽约小说中的婚姻主题,揭示了这些贵族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的从属地位,进而观察其反抗的声音以及日益增强的女性自我意识。程心的《时尚之物:论伊迪斯·华顿的美国“国家风俗”》描述了昂汀从时尚的跟风者到拥有者再到操纵者的过程,指出昂汀的时尚行为展现了美国女性消费时尚之物同时也被时尚消费的困境。李玲娜、张俊萍的《试论伊迪斯·华顿小说〈国家风俗〉中的新贵伦理》指出以昂汀、莫法特等为代表的新贵阶层的伦理观既不同于以家族利益为先的上流贵族,也不同于崇尚“经济实用”的下层社会,其伦理取向具有独特性。许辉、郭棲庆的《〈国家风俗〉中双面性的安丁形象解读———从叙事视角谈起》关注小说中的多维度视角的切换所展示的华顿对20世纪初期美国家庭、婚姻、道德等社会问题的伦理思考。
上述研究成果从婚姻、时尚、新贵伦理等角度,将论述的重心放在昂汀或以昂汀为代表的新贵阶层,探讨这一阶层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消费主义盛行的美国文化的促进和冲击。然而,不仅是新贵对物进行操控和依附以实现自我主体身份的建构,老纽约贵族们透过对古物的情感折射以逃避现实,渴望通过对传统和过去的怀旧性诉求实现在现代性中的自我救赎。本文试从《国家风俗》中的新旧之物出发,对比小说中新贵阶层渴望透过物的收集和物所折射出的象征性符码意义而建构缺失的自我主体身份,以及走向离散分裂的“老纽约”贵族通过对古物的愿景投射而实现对往昔的见证、回忆、怀旧和对现实的逃避。然而无论是以昂汀为代表的新贵还是以拉尔夫为代表的“老纽约”贵族,在这样一个没有稳定的意义准则并将物的符号价值看得高于一切的社会中试图证实自身的独特性是徒劳的,因为独特性在此不会长久保持。
比尔·布朗在《物的意义》中指出,“正是由于美国没有所谓的有闲阶级才导致了凡勃伦所描述的效仿性竞争。也就是说正因为没有稳定的阶级标签(没有等级制度)才迫使主体进行自我标识”,他们“保持光鲜的外表”或“以一种伪善的美德或道德正直的保护层来掩盖他们的一举一动”。这正是为何在华顿的《国家风俗》中,昂汀·斯普拉格对华丽的服装、珠宝、酒店无休止的追求,甚至以冷漠的态度更换一任又一任丈夫;也正是为何她的两位前夫拉尔夫马维尔和雷蒙德·切尔斯对家族遗物忠贞不渝地坚守。他们对物的执着揭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造成的错位影响破坏了传统伦理结构的‘象征效力’(symbolic efficacy),产生了一种社会道德真空”,导致了一种不断流动变化的状态,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都竭力渴望爬上社会阶梯的顶端,而老牌的财富和权位占有者则进行防御,以抵抗那些想要获得社会名望的新富们。20世纪初,金钱赋予人们更多获得和操控物的机会,同时不断地游走于物与人的关系中,使人渴望透过与物的关系来恢复自我认知及自我身份建构的能力。
华顿《国家风俗》中的物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们得以观察小说中的新富阶层和上流社会为何以及如何利用物来构建意义,透过物来创造或再造自我,组织他们的焦虑和情感,升华他们内心的恐惧并塑造他们的幻想,以期填补因缺乏贵族阶层的身份所做的徒劳努力。小说中的两方势力代表都试图通过“愿景构建”而获得稳定的身份,却不可避免地以重回弥漫在现代性历史中的虚无主义而告终。
一
身份建构:奢侈品的收集
坡在他的“家具哲学”中宣称,“美国人的品位是‘荒谬的’(与英国人、荷兰人、中国人或西班牙人相比),因为我们‘没有贵族血统’,只能用粗俗的努力来代替,以期与众不同。”昂汀·斯普拉格通过对物的收集来建构她从未拥有过或已经永远失去的主体性身份。对昂汀来说,不是通过物的生产而是物的积累和炫耀来获得成就感和认同感,也就是说她对身份无意识的追求更多地依赖于他人对她所拥有的物的认可,而不是依赖于物本身的使用价值和功能。
在迫使父母和她一起离开埃佩克斯来到纽约前,“昂汀就已透过第五大道的丰功伟绩和千姿百态来塑造自己温柔的想象。她知道纽约所有黄金贵族的名字,而纽约最显赫家族后代们的外貌也因她对每日报纸热情的关注而变得熟悉起来”。她对服装、珠宝、酒店和旅游目的地的疯狂收集带给她一种胜利感,这是她个人享受的必要前提。“对物的拥有似乎是她生存的第一要素”。“个人欲望”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每个所谓“个性化”的物对昂汀的吸引和诱惑。这些物似乎赋予了她个性、活力与生命。然而,昂汀疯狂地渴望独立却又满怀激情地热衷模仿,她对物的获得充满欲望并不可救药地仿效他人。她想通过自己的大胆和创新使身边的每一个人惊讶叹奇,却情不自禁地模仿她遇到的任何一个人。当她在一家画廊看到一位女士透过挂在长长的珍珠链上用钻石装饰的玳瑁眼镜欣赏画作时,“似乎用肉眼看世界顿时变得廉价而平庸,似乎她所有流淌着的欲望都汇集成对用珠宝装饰的眼镜和挂链的渴望”。
昂汀诉说的是一个“占有”的故事,或者可以说是被所有物占有的故事。她对占有奢侈品的这份热衷不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而更像是一种欲望的满足。无论是昂汀,还是她的第三任丈夫莫法特,一位被通俗报刊称为“纽约最杰出收藏家”的商人,在凝视物的时候,都充斥着一种满足感。他们对物诉说的不是一种对艺术的赏析,而是一种占有的欲望。“收藏物是一面镜子,它所忠实反映的,不是人的真实形象,而是人对自己所欲望的形象”。莫法特和昂汀“收藏”的正是自我塑造的碎片,他们渴望通过收藏重新建构一个完整的自我主体。对莫法特和昂汀这样的收藏者来说,物的展览价值一如既往地要比任何交换或使用价值重要得多。或如鲍德里亚所指,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结构中的消费品系列,“是一整套消费品之间存在的必然有序性关涉,其间起根本性支配作用的东西,就是由符号话语制造出来的暗示性的结构性意义和符号价值(风格、威信、豪华和权力地位)”;在消费关系中,消费者的需求瞄准的“不是物,而是价值。需求的满足首先具有附着这些价值的意义”。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人们今天在消费中更受吸引的不是物品本身的功能,而是某种被制造出来的象征性符码意义。人们对商品的消费不再满足于对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消费,而更加关注商品附加的文化内涵与等级差异。如作为新贵代表的莫法特热衷于收集那些无与伦比、极具代表性的收藏物,以使他在别人的眼中与众不同,从而获得或弥补他和昂汀都缺失的主体性身份。他与昂汀最享受的时刻即自己在众人的赞赏中显现出个人魅力的时候。为了得到他人的认可和关注,他们习惯性地拒绝为自己的想法承担责任,总是倾心于外表精美的物,并本能地将自己塑造成他人渴望自己成为的样子。而对他人,他们则呈现一种道德真空和道德惰性。正如昂汀的好友印第安娜所说,“是纽约生活让你丧失了道德感”。每当昂汀对物的欲望得到满足时,她总觉得“终于得到自己想要的了———她总是有意识地占有‘真实物’(the ‘real thing’)”。
在收集物的同时,昂汀还“收集”丈夫。她更换一任任丈夫的唯一理由和前提就是他们必须能够满足她的物质需求:买她想买的东西,去她想去的地方,让她成为其他女人嫉妒的对象。昂汀实际上是想通过购买东西的行为外化自己。因此,她无法理解拉尔夫的理想,也无法分享拉尔夫古老家庭的关键词:优雅、自豪和个人尊严。最终,拉尔夫发现“她(昂汀)的思想就和她受教育的牧场校舍那样缺乏美感和神秘感;而她的理想就如她儿时用软木塞和雪茄衬带做成的手部饰品一样乏味可怜”。对昂汀来说,她企图通过对物的疯狂占有来弥补她从未真正拥有的过去和身份。然而,昂汀在占有物的同时却忽略了自已被“物化”的事实。昂汀对物的疯狂,其实正是她渴望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渴望一个固定身份的症状外显。对一个行为的不断重复标志着对生活的可控性、稳定性或停滞性的渴望。消费欲望(如百货公司的建立)之所以能成功产生,“是因为消费、占有、积累和炫耀成为人们能够解决居于一个民主国家这一结构性事实所带来的本体论困境”。对物(如饰品、装饰物、礼品)的大量积累起到了某种“补偿功能”。对昂汀来说,她企图通过对物的疯狂占有来弥补她从未真正拥有的过去和身份。
布朗“将存在于真实物中心的空洞定义为‘大他物’(the Thing)。这种空洞表现为一种虚无,一种‘零’的状态”。这些被收集的物本身创造了这一空洞,并提供了填充这一空洞的可能性,但最终却还是一种徒劳的幻想。在物的迅速扩张中,“大他物”总是处于缺席的状态。如齐泽克所说,“消费主义的对象———物件(object-gadgets)因承诺带来过量的愉悦感而吸引着力比多,但其真正带来的却只是匮乏本身”。人类痛苦的根源在于对物的不可抑制的渴望,然而即使最终得到了,却也无法真正满足他们。因此,当昂汀拥有了她所渴望的一切时,她却时不时地想着也许还有其他一些她不知道的但她可能想要得到的东西存在。波德莱尔也在他的《玩具的哲学》一文中提到,“孩子最大的渴望是能窥探玩具的灵魂,这是他们所经历的‘第一个形而上学的倾向’:正是这一倾向,这一欲望促使孩子在玩具被摧毁被剖开的那一瞬堕入‘忧郁和沮丧’之中。这也是人们面对缺失灵魂的当代生活的标准反应,也是告诫人们欲望之物并不足以带来满足感的教训之一”。因为“我们收集身边之物的能力与我们对这些物之体验能力成反比”。
二
愿景构建:“古物”的收集
如赫顿和爱德华在《美国文学思想的背景》中所言,“在镀金时代的金融喧嚣中出现了高雅传统的冷静感伤,表现为其表面的优雅、消极的道德感,可悲而无力地试图在一个粗鄙的物质世界中注入一丝良好的教养”。在《国家风俗》中,昂汀的第一任丈夫拉尔夫·马维尔则是这一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拉尔夫是达戈内特家族的后裔,在昂汀的美甲师希尼太太(她从剪报中获得了关于这些“杰出”人物的所有信息)看来,他比来自纽约其他家庭的任何年轻人都要“光鲜”。拉尔夫唯一的信条是“要像绅士一样生活———对单纯为赚钱而活的暗暗蔑视、对细腻情感的被动接受、掌握一两个关于品酒的固定原则、保有一种不懂区分个人和‘商业’荣誉的老派正直感”。
与昂汀不同,拉尔夫以一种家族传承而来的“正直感”享受平静与书本。他珍惜家庭关系和家族遗物,将它们视为历史和记忆的体现。因此他试图通过对古老而熟悉的物进行想象框架的投射以保存传统并构建身份。如昂汀的第二任丈夫雷蒙德·切尔斯竭尽所能维护家族城堡一般,拉尔夫对华盛顿广场的祖屋有着特殊的感情。从拉尔夫最早的记忆开始,他的母亲和老厄本·达戈内特先生似乎就与华盛顿广场的祖屋融为一体,“他们可能将其看作自己内在意识的体现,正如祖屋可能代表了他们的外在形式一样”。这也是为何当昂汀建议切尔斯卖掉城堡时他勃然大怒并对她逐渐冷淡的原因。昂汀的建议“给了他一个可怕的、近乎恶魔般的意味深长的暗示:似乎她不经意的几句话让他终于明白了他们之间不幸的根源以及他们之间本质上的差别”。对切尔斯和拉尔夫来说,这些古老的建筑历经沧桑,世代相传,凝结着几代人的焦虑和抱负。透过第五大道另一端截然不同的建筑面貌所体现的社会分化和解体,这些古宅印证了它们存在的内在意义。这些古宅代表的是时间,它们“与功能计算的要求相抵触,它们回应的是另一种意愿:见证、回忆、怀旧、逃避”。通过它们,离散分裂的人似乎寻找到了一种感情的幻想投射。对拉尔夫来说,与祖宅同样重要的是代代相传的传家宝。在昂汀眼中,丈夫送她的蓝宝石钻石戒指只不过是一个值钱的物件,是她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任意翻新甚至在自己需要钱来购买更多其他花哨物品时可以贩卖的一件商品。而对于拉尔夫而言,祖传的戒指在经历了几代人的生活后拥有特殊的意义。对他来说,这个戒指不是普通的物件,而是被赋予了特殊的情感和意义。布朗指出,“精神的生存依赖于对物的世界意义的赋予。如抽屉、箱子、衣橱被看成是‘内在精神生命的真实组成部分’,它们是作为现象学的假体而存在,为人们提供‘亲密的意象’,为人们的‘亲密生活’提供一个模仿的样式”。因此拉尔夫将祖传戒指作为订婚礼物送给昂汀,他渴望在这枚戒指中嵌入他这一代人的生活痕迹,并将其继续传承,从而实现家族精神的传递。“使拉尔夫伤心的是昂汀根本意识不到当她毁掉了戒指作为传家宝的内在意义时给他和他的家人带来的伤害”。正如切尔斯对昂汀的控诉:“你来到我们中间,说着我们的语言,却根本不了解我们要表达什么;想要得到我们渴望的东西,却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想要;模仿我们的弱点,夸大我们的愚行,忽视或嘲笑我们所关心的一切”。拉尔夫和切尔斯逐渐意识到昂汀是一个无法“联接”或融合的“他者”:她来自像城镇一样大的旅馆,来自像纸片一样脆弱浅薄的城镇,那里的街道还没来得及命名,建筑物还没干透就又被拆毁重建;那里的人对待变化如同我们对待自己坚守的东西一样自豪。“我们还愚蠢地认为,他们模仿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随手学了点我们的语言,就能真正理解那些让我们的生活体面而可敬的东西”。对拉尔夫和切尔斯来说,祖宅和传家宝是能够使生活体面和可敬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在这些物件上,凝聚着对过去的记忆。他们对一个充满希望和可能的未来的愿景也被投注在这些物上。正如阿兰特所说,“世上的物具有稳定人类生活的功能,其客观性在于,尽管人处于千变万化的状态中,却能通过与同一把椅子同一张桌子间的联系而重获他们的同一性,即他们的身份”。
然而,拉尔夫和切尔斯对古物的珍视本身也体现了他们对自身所处现实的一种无可奈何。血统、出身和爵位在小说中描绘的“纽约”已然失去了它们的意识形态价值。对于此时的纽约,物质性的符号才具有表达卓越的任务。拉尔夫和切尔斯的古宅和古物体现了一种“既非内在、亦非外在,而是‘不在’———它既非共时性,亦非贯时性(它既不进入一个气氛的结构,亦不进入一个时间的结构),而是时代错乱”。因此,这些古宅和古物,“与其说是拥有之物,不如说是象征上有善意影响力的物品”。当古物指涉过去时,它不再拥有实用价值,而是完全作为符号存在的。透过古宅与古物,拉尔夫和切尔斯实现的是一种对现实和日常生活的逃避,“而逃避只有在时间中才能最为彻底,也只有在自己的童年中才最为深沉”。
当拉尔夫试图填补“真实物”和“现实”之间的空隙时,他所处的社会注定要将其歼灭。他就像一个穿着中世纪盔甲的现代人:拉尔夫的存在本身即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体,尽管谨遵家族传统和价值观,拉尔夫仍然感受到来自它们的束缚以及来自暴发户们的威胁。他有时称他的母亲和祖父为土著人,将他们比作那些随着入侵种族的推进而注定要迅速灭绝的美洲大陆上正在消失的居民。他喜欢将华盛顿广场的祖屋描述成“保留地”,并预言不久它的居住者就会出现在人种学的展览中,可怜地从事着他们的原始作业。在拉尔夫自由自在的青年时代,他激昂地反对自己所处阶级的习俗。然而,当他真要去蔑视或抛弃这些习俗的时候,“它们却不可思议地占据了他,就像某种隐性的遗传缺陷一样使他偏移了方向”。当他重新审视这一切的时候发现似乎连他人生中最大的不幸都已经被他所继承而来的关于优雅、自豪和个人尊严的价值观所惯例化和感伤化了。他鄙视那些有钱但粗俗的家伙,比如彼得·范·德根和埃尔默·莫法特。然而,他无法否认的事实是,这些人已经爬上了更高的社会阶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甚至一些有教养的人也向他们投去了艳羡的目光。他厌恶为了讨生活而工作,然而,他的姓氏带给他的只是表面上的荣耀,却没有多少实在的利益。如拉尔夫的姐夫鲍恩所说,“可怜的拉尔夫是个幸存者,因此注定要在与新兴上升力量的任何冲突中被击败”。曾经赋予他稳定感的不可剥夺、不愿交易的家族遗物成了新贵们竞相收集的消费物,他所传承的价值观和传统注定被抛弃得无影无踪。他发现古屋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对生活种种无谓的障碍。他生命中唯一真实的两样东西,也是他和过去以及将来相连的纽带———儿子和那本一直处于写作中的书———的痛失对他的打击不仅是身体上的,更导致了他的存在危机。他所继承的仪式和惩罚的古老结构都瞬间坍塌。他发现不仅是古屋作为物本身,还有它所代表的社会价值观,都使他窒息。“甚至一想到要在这片混乱中清出一点空间对他来说都是极其费力的任务”。以古屋为情感和愿景建构媒介作为自己重获身份、重拾过往的方式对拉尔夫来说成了幻影。
对于拉尔夫来说,传家宝以及祖传的房屋和物件不仅仅是简单的物,而是他在面对这样一个暴发户新贵不断爬向社会阶层高处的文化中,对传统和过去的一种怀旧性诉求。拉尔夫试图以“老纽约”所珍视的品德引导昂汀的行为,帮她辨别哪些交往是得体的,哪些交往是应谨慎避免的。他幻想着昂汀能够理解承载在家族物质和精神传统中的意义。然而,昂汀却只会对看得见摸得着的物感兴趣。拉尔夫的死表明他愿景构建的最终失败。齐泽克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沉浸在由幻想构建和支撑的‘现实’中,但这一沉浸往往使我们对那个维系着与现实之间联系的幻想架构视而不见”。齐泽克定义了日常现实(the reality,即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由既存习惯与观念构成的社会空间)与实在物(the Real)那残酷而无意义的创伤经历之间的分裂。拉尔夫的悲剧,回溯性来看,也是源于他的愿景构建所导致的对“实在物”和“日常现实”的混淆。
三
结语:空洞的物
华顿在她的小说中“痛斥了一个所谓文明国度的虚伪做作,这一民族的文明假象无法遮掩肤浅者的成功和对原始状态的颂扬”。然而在一个只热衷于占有金钱却不知如何合理消费的文化中,“成功可能和失败一样令人疲惫”。无论是昂汀还是拉尔夫都渴望通过对物的操控和依附来实现在现代性中自我的救赎。对昂汀来说,她渴望通过对物的疯狂收集以及无尽的流动状态来把握生命的意义,从而获得主体性与自我身份。对拉尔夫来说,对家族遗传的物的珍视体现了他渴望重获和恢复过去的传统与身份,从而为被金钱的闪耀外表所魅惑的社会提供一剂治愈的良方。然而昂汀和拉尔夫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纽约是现代性罪行的暴露场,而现代性罪行的实质是透过金钱对新奇事物的不懈追求。华顿小说中的纽约竭尽全力阻止真诚与情感的扎根。现代性受资本和实用理性的驱使,极力阻止物拥有物性,阻止人们获得除了商品使用和交换价值外的任何其他价值,使物丧失生命力,将其圈囿在商品拜物教的藩篱内。如海德格尔所言,“物的物性被商品外在形式的霸权所摧毁”。无论是昂汀还是拉尔夫都模糊了拥有(having,占有某个具体的物)和成为(being,透过物来识别自我)之间的界限。对于他们来说,概念化或想象化的物要比“能用手摸到”或“用眼睛看到”的物具体有效得多。他们的例子讲述的是物在身份建构中的作用,尽管对昂汀和拉尔夫来说,将愿景构建投注到物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昂汀与拉尔夫对物的不同态度,与其说是夫妻间人生观、价值观的迥然相异,不如说是现时性与历史性、具体与抽象、粗鄙与教养、新贵与传统、瞬息与永恒间的一场较量。人所缺乏的,总会被投注到物品身上。昂汀和拉尔夫对物的收集其实是对自身缺失的要素的物质化过程。因对古物的追忆而“向后看”的拉尔夫是当下的“发展落后者”,因而对他而言,在古物身上被神化的是威能,而过度关注物的功能性因而“向前看”的昂汀便是拥有技术的“现代人”,对其而言,被神化在奢侈品和形形色色的物上的,则是出身和真实性。然而,无论是昂汀还是拉尔夫,在这个新旧交替和并存的时代里他们遭遇的是文化身份和归属感的缺失,因而无法在这个新颖与过时、永恒与瞬息并存的新时空压缩体中生存。在经济发展、工业生产、环境的实用性饱和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出现这种功能性的现代物体系和古物间暧昧与冲突的共存。昂汀和拉尔夫分别通过收集具有炫目形式的奇特物品和充满了过去记忆的古老家族遗物,拼命想在这样一种新旧交替、融合与冲突的文化中建立或重获他们的主体性,却发现这一切努力都是填补空洞的徒劳努力,一切终将重归虚无。

学术为公 学术为先
国内连续出版物号:CN32-1593/C
国际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105X
邮发代号:28-444(欢迎订阅)
联系电话:0516-83885569
期刊网站:http://xb.cumt.edu.cn
E-mail:xbsk@cumt.edu.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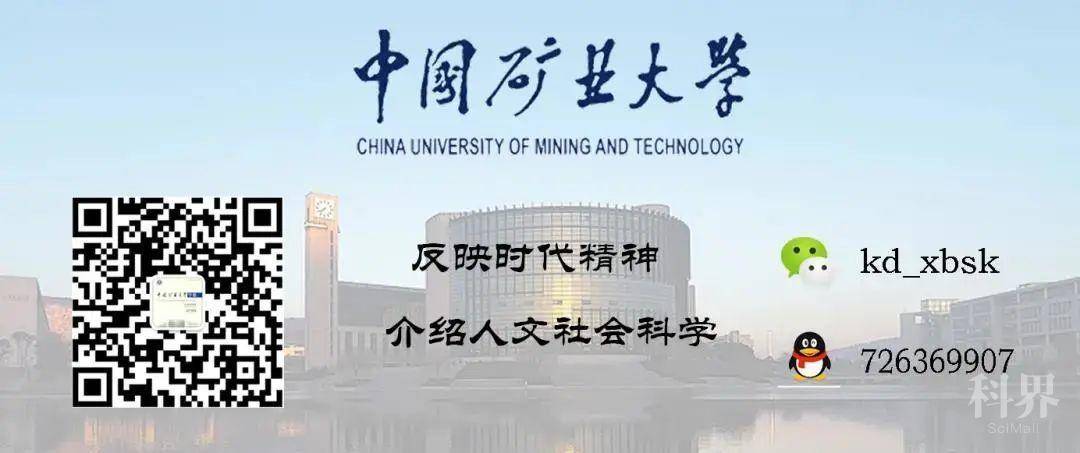
来源:kd_xbsk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原文链接: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TY4MjY1NA==&mid=2650960809&idx=1&sn=27f1fd16cf3d3d8df86d7d5b7f967673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注明,本站所载内容来源于互联网、微信公众号等公开渠道,不代表本站观点,仅供参考、交流、公益传播之目的。转载的稿件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电话:(010)86409582
邮箱:kejie@scimall.org.cn